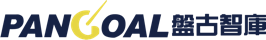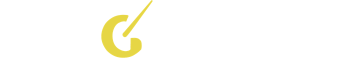熊炜:德国对华政策转变与默克尔的“外交遗产”(上)
长期以来,人们注重在双边关系维度上观察德国对华政策,聚焦于德国对华政策如何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两者之间摇摆,而忽略了从国际秩序演变和德国崛起的大战略维度来分析德国对华政策以及中德关系的发展。当今国际体系面临深刻转型,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观基础和制度框架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侵蚀,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德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却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显著的上升。因此,当前德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一个崛起大国针对另一个崛起大国的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全球战略意义,而中德两国又遵循着不同的崛起路径,中国是从西方主导体系的外围向中心突进,而德国则是从西方体系的内部自下而上崛起。
德国对华政策目前正经历从“建设性接触”到“现实性接触”的战略转型,它改变了过去所谓“以商促变”的对华政策,不再寻求改变中国,转而宣示双方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明确两国关系的性质是相互竞争的,冀图在开展经贸合作的同时利用规范、规则和制度来制约中国。本文探讨德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认为这并非德国对华政策在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又一次摇摆,而是德国崛起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德国现在是以西方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和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首席代言人”身份来实施对华政策,而且作为默克尔的“外交遗产”,其对华政策的新战略框架也将为2021年大选后的德国政府继承和发展。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战略视角重新审视德国的实力,并评估德国对华政策战略转变的意图及其对中国外交带来的新挑战。
一、德国对华政策转变∶从“建设性接触”到“现实性接触”
2020年9月2日,在王毅国务委员结束访问德国的次日,德国政府即颁布题为《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 21世纪》的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指针》)。这份文件名义上虽然是印太政策指针,但实质上却是以间接方式建立德国对华政策新战略的轮廓。在这份文件中,德国政府首次使用了富含地缘战略含义的概念——“印太”,区别于以往用地理概念“亚洲”或“亚太”来指称其亚洲政策,而此前在 2017年,德国外交部为表示对亚太地区的重视,还曾增设了亚太司。德国官方使用“印太”概念是追随美国对亚太地区地缘竞争格局的重新定义,2017年特朗普政府曾提出美国的印太战略,意图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以美、日、印、澳四个所谓民主国家为核心联手遏制中国的崛起。德国现在认同这一概念,其目的也是要从地缘战略上应对中国,但其印太政策构想在内容和路径上又明显区别于美国以军事安全战略为主的导向。德国强调要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同时暗指“中国经常不遵守国际规则”,表明德国希望以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为基础在印太地区发挥其“塑造性权力”。
针对中国,《指针》明确表达了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诉求,提出德国有必要实现在印太地区的发展合作关系多样化,与该地区价值观相同的伙伴的合作尤为重要,并将提升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的分量。虽然印太地区许多国家或经济体在很多方面的重要性远不如中国,但《指针》表示将通过与更多伙伴加强合作来推动印太地区的多元化发展,与德国价值观相同的印太地区民主国家被确认为优先合作伙伴。以《指针》为标志,再联系德国政治家最近的各种表态,可以看出德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框架已经改变。
传统的德国对华政策以“以商促变”为关键词,实施对华“建设性接触”战略,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德国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获取经济利益;二是通过经济合作和人文交往,促进中国的政治变革;三是推动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引导中国做“负责任”的国家。这同时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华政策普遍采取的传统战略框架。但是近几年中国快速发展和国际秩序加速转变,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认为,通过传统的“建设性接触”战略,已无法按照西方的预期推动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与此同时,中国尝试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之外建构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中国外交日趋主动,也给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带来了冲击。在此背景下,美欧对华政策普遍酝酿调整。不过,与美国特朗普政府转向对华全面“对抗”和“脱钩”有所区别的是,德国意图对华实施一种被《金融时报》称为“现实性接触”的战略。
外交上所谓“现实性接触”战略,肇始于冷战时期,主要包含如下要素:第一,承认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的分歧与差异,不寻求改变对方;第二,明确在实际合作领域中的共同利益和其利益交汇点的界限,不盲目扩大合作;第三,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展开对话和合作,防止对抗。“现实性接触”和“建设性接触”战略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合作和互补的,而是认为两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不可改变,两国关系的基础是相互竞争的,但需要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对话和合作。在“现实性接触”的框架下,德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不再是为了改变中国,而是要在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同时,强调西方价值观,利用规范、规则和制度来制约中国的行为。
虽然具体的内容还有待充实,但是未来德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战略框架已经显现出来。作为“现实性接触”政策,德国将保持与中国的合作与接触,不会像美国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那样“脱钩”,但是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明确差异,将中国定位为“对手”,而且敢于“斗争”。在经济上强调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者的双重定位,在寻求对华合作谋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防范中国的竞争,以“对等”为名义,扩大对中国市场的进入,与此同时推动欧盟对外资进入的审查,强化数字主权,保护德国未来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产业竞争力。在气候变化、全球发展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对话合作,鼓励中国多做“贡献”。
二、“意识形态偏见”抑或“战略转变”?
“现实性接触”战略明显强调中德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以此作为出发点建构对华政策。有人或许认为德国外交的这一转变是意识形态偏见所驱动的,例如可能是全球疫情蔓延大背景下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凸显的一个具体表现,或者也可能是德国国内长期以来对华政策在利益和价值观之间摇摆中的又一次意识形态因素暂时上升。这种判断实际上也暗含了德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摇摆性质——在外部冲击结束或内部平衡变化之后,天平还会再次摆回来。
仅从印太《指针》反映出来的思路来看,其中很多内容确实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在 2007年推出的一份名为《作为德国和欧洲的挑战与机会》的亚洲战略文件有许多相似之处。2007年的文件认为,中国崛起引起世界巨大变化,并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各领域对德国和欧洲构成巨大挑战。特别是在德国眼中,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民主、不自由,但是经济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对西方构成了“体制挑战”。当时联盟党提出的应对策略是,应改变德国以往亚洲政策的“中国中心”,寻求与所谓“亚洲民主国家”建立基于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合作,称“只有在扩展和稳固建立人权、法治国家、社会公正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期望在一个亚洲和西方都可能发挥影响力的未来世界秩序中,能够(与亚洲)分享对人类未来的认识,德国和欧洲人的利益也才会被适当的对待”。虽然在默克尔的第一任期内,她也曾设想将这种意识形态驱动的对华政策付诸实施,例如于 2007年 9 月示威性地在总理府会见窜访欧洲的达赖,导致中德关系跌入低谷,紧接着又在 10 月出访印度,在新德里大力宣扬“价值观外交”。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令德国和欧洲对华需求增强,默克尔的对华政策又不得不摇摆回实用主义利益驱动的传统。而且此后中德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以至于在默克尔第三任期开启之后,德国智库甚至把默克尔此前领导德国的十年称为“中德合作的黄金十年”。因此很多人认为,对德国政治家近期的言行也无须大惊小怪,德国对华政策最终还将像 2007-2008 年那样回到经济利益驱动的旧轨道。
另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德国意图转变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对自己“改变”中国能力的现实评估基础上,而非主动的战略转变。近年来,中德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被称作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超级大国”,而德国的 GDP 只有3.85 万亿美元,远远低于中国的14.34万亿美元和美国的21.37万亿美元,军事实力更是无法相比。面对“超级大国”中国,作为“中等强国”的德国不得不放弃通过所谓“建设性接触”对中国进行“改变”,实施“现实性接触”只是德国面对变化的现实而不得不做的自我强调和保护。
但是,本文认为德国对华政策在当前的转变既非其基于现实的无奈之举,也不是一时的意识形态转向,而是德国外交在战略意义上的转变。这里的“战略”是指德国崛起的大战略。虽然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德国官方慎言“战略”和“崛起”,但是德国却从国际社会的“二等公民”成功发展为世界大国,相比于当代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升之路,德国崛起的速度和幅度都毫不逊色。它即使不宣称所谓崛起战略,但实际上也有着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大战略”。在实践中,德国崛起的特点是选择了“嵌入式崛起”战略,即将自身嵌入西方国际秩序之中,在努力保持嵌入状态下,积极寻找崛起机会与空间,寻求在体系内部由下至上的成长而非由外向内的崛起,崛起的目标是成为西方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维护者。因此,目前的中德关系在实质上是两个遵循不同崛起路径的崛起大国之间的政策互动。
在德国崛起的大战略中,中国的战略位置和作用明显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中国是德国的经济合作伙伴,德国对华实施“建设性接触”战略,通过“接触”和“引导”中国,│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加强了自身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充当“掮客”(Broker)的身份,而现在德国崛起的目标已经由寻求成为“正常国家”转变为西方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因而中国作为西方政治体制竞争的“对手”和身份认同的“他者”,成为德国强调自身作为西方领导者角色的对立面。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不再是双边关系意义上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转换,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事关德国崛起大战略目标的实现。
而且,德国其实是将中美“对抗”、美国推行与中国“脱钩”的政策视为德国“崛起”的契机,德国因而有机会在西方世界填补美国出让的局部领导权真空。为此,德国需要一方面代表西方与中国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划清界限,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所谓“体制性挑战者”,但另一方面又要替代美国对中国实施接触政策以保持现有体系的稳定。这就意味着,德国将从局部接管美国的领导权和防范中国对西方的挑战这两方面同时着手,以成为西方价值观以及规范体系的首要代言人和西方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从而实现崛起。
(一)中美“对抗”是德国崛起的战略机遇
当前国际体系“乱象丛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领导权真空”。一方面,中国崛起和发挥全球性影响引发美国的猜忌和强烈反推(push back)效应,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明确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先是挑起中美"贸易战",继而宣称要与中国“脱钩”,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安全等领域“对抗”,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一时难以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奉行“美国至上”和单边主义,频频“退群”,正如《纽约时报》评论称,特朗普“用‘大锤’破坏了美国历届总统亲手缔造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特朗普所作所为的实质是放弃美国对西方国际秩序的领导权,美国不仅缺乏领导国际秩序的意愿,而且作为“守成国”破坏了由其自身发起建立并长期维护的国际规则,导致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威大大降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秩序“失序”显示出的领导权真空并非传统的基于强制性权力基础上的实力真空,也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的大幅衰落而出现的,确切地说,是基于国际规则被破坏而导致的规范缺失的领导权真空。因此,填补这一领导权真空并不需要建立强制性权力意义上的领导权,而是需要在国际秩序的规范和规则方面建立权威,德国和欧洲则在这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相比于美国等传统强国,德国和欧盟擅长通过思想和观念的力量以塑造其他行为体的价值观,利用规范传播来完成原本需要军事或者经济手段来实现的对外政策目标。正如德国外长马斯在一次讲话中所说,美国政策和国际秩序的转变早在上届美国大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也将在下一届美国总统产生之后延续,而对德国和欧洲非常确定的一点是:欧盟必须在全球大国竞争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同时,在中美“对抗”的格局中,美国和中国显然都想拉住德国,这客观上也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中国向来重视德国和欧洲在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维护世界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尤其注重发展中德关系为运筹中美关系创造条件。而在美国对华施压的过程中,即便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意识到德国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德国和欧盟国家的合作,美国将无法应对中国的挑战。例如,从特朗普政府的角度来看,出口管制是与中国抗衡的重要手段,但只有欧盟配合,美国对华实施出口和技术管制的措施才会奏效。因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利(Josep Borell)在2020年6月25日向美国提议就对华政策建立欧美对话机制,美国随后积极响应,并期望产生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更加协调一致的政策结果”。
显然,中美“对抗”的趋势扩大了德国的战略空间,德国在维护西方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更加明显。在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其实一直希望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发挥大国作用,但却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和主导国的限制。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显示,德国受到的国际体系束缚正在减少,而且在中美两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竞争的同时,德国却在以另类方式实现更迅速的崛起。
(二)德国冀图抓住机遇
2019 年以来,德国积极参与全球外交,在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极为高调,领导欧盟频频发声。与以前德国外交奉行“低调”“克制”原则明显不同的是,德国更加明确宣示大国雄心,要在“世界上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这些都显示出德国想要抓住当前国际秩序出现领导权真空的契机,实现德国崛起的意愿。德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是要成为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其领导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捍卫西方秩序的规范、规则和理念基础上。
面对美国,在 2020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多次抨击美国背离“国际社会”,德国外长马斯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正是美国“逃避了维护西方秩序的责任”。而针对中国,德国政要则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以西方国家“发言人”的身份攻击中国。2017年,施泰因迈尔在新加坡发表演讲称,西方国家恐惧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和美国的不确定性,“中国对西方是一个挑战”,不仅在经济上和地缘政治上,而且也在意识形态方面;2018年2月,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称:“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全面的替代体系,这不同于我们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西方体系。”
在外交实践中,德国亦有创新之举。它于2019 年4月首倡“多边主义者联盟”计划,意图联合西欧、北美以及亚洲部分国家,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多边主义者联盟”计划的内核由所谓的理想主义合作伙伴组成,包括法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三个最核心的国家,外层则主要从实用主义出发,团结可以团结的认同西方理念的国家。德国外长马斯在德国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称:“其他国家越是倚重强权,我们越要坚定地倚重多边秩序。”这个联盟应齐心协力支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问题,支持联合国这类国际组织继续发挥强大作用,强调联盟的“大门尤其对美国敞开”。“多边主义者联盟”是一个非常设的国际机制,与传统多边机制不一样的是它没有明确的功能,中短期内似乎也不会有明显的国际政治效果,但是德国发起这一联盟的时机和所表达出来的指向却耐人寻味。它既有对美国的期待,也有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防范。德国发起倡议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其有意发挥在西方世界的领导作用。
与此同时,德国更加注重在欧盟内部的领导作用,加强整合欧盟的外交资源。长期以来,德国痛感欧盟难以在国际舞台上以“一个声音对外”,限制欧盟全球影响力的发挥。无论是面对美国的压力,还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德国认为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均在特定议题上存在“分裂”现象。然而,中美“对抗”的新格局对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对华政策都带来新的挑战,欧盟主要国家普遍认识到必须以此确定新的坐标系,因而加强欧洲内部整合的迫切性十分突出。因此,在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明确表示,德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义务就是“将欧洲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德国加强了支持欧盟对外行动署、欧盟委员会等欧盟机构的行动,推动欧盟在各个层次上实施“相互协调、目标清晰和更加团结”的对华政策。2020年以来,德国主导深化了欧盟27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非正式协调机制,2月在柏林首次召开了欧盟27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欧盟机构代表之间的对华政策协调会议。
总的来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强烈冲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权威的衰落,西方世界出现了部分“权力真空”,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对“西方失势”的忧虑,对德国发挥领导力具有强烈期待,甚至有媒体评论称:“默克尔是西方衣钵的继承者,是欧洲最后一位还站着的领导人,有责任代表过去 70年里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西方发言。”在此背景下,德国崛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德国转变对华政策的长远意图,其核心是谋求建立区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战略新框架,一方面代表西方对中国展现强硬,另一方面替代美国实施对华“接触”,并由此塑造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应对中国,从而实现德国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领导权。德国对华政策虽然目前只是在战略框架上的转变,具体内容和实施路径尚未明晰,但作为德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的意义。(未完待续)■
标签
推荐阅读
-
熊炜: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与困境(下)
2021年02月25日 -
熊炜: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与困境(上)
2021年02月24日 -
熊炜:德国对华政策转变与默克尔的“外交遗产”(下)
2021年02月18日